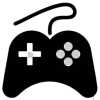在上世纪80 年代的内地影坛,陈国军曾是备受瞩目的风云人物。
他曾跻身于新时期最受欢迎的明星行列,主演的《药》《心灵深处》等影片脍炙人口。他是最早演而优则导的突出代表,由演员转行做导演,执导的电影《无情的情人》《大清炮队》曾轰动一时。他是最早一批从电影界转型涉足电视剧领域的导演,拍摄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末路》《威胁》等电视连续剧屡获大奖,并创造过万人空巷的收视佳绩。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内地娱乐圈,陈国军曾是颇受争议的焦点人物。
他是最早的“娱乐红人”,他与著名影星刘晓庆的恩怨聚散,一度成为人们街闻巷议的热门话题。他是明星写自传出书的先驱,一本《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曾洛阳纸贵。他也是最早的遭遇“被动式”娱乐炒作的受害者,生活被聚焦,艺术却失焦。
四十多年的内地文艺舞台,风云变幻,尘埃落定。身为领风气先和主要见证者,陈国军回首往事,感慨万千。面对一波三折的演艺生涯,任何旁观者华丽语言的描述描写,都不及亲历者真挚情感的娓娓诉说。面对刘晓庆这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任何外界的迂回揣度和肆意猜测,都比不上当事人“是非恩怨皆看淡,只留祝福在心间”的姿态和状态来得洒脱。
通过陈国军的讲述,透过流短飞长,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个人性情与个人才华被娱乐绯闻淹没、人之常情及世俗情感被流言蜚语遮蔽的陈国军。
《心灵深处》成演艺生涯转折点
童年经历对性格的塑造影响至深,童年生活对于一生所走的道路影响很大。您如何看待童年生活和演艺人生的关系?
艺术家罗丹曾说过一句话:什么是美,真实就是美,自然就是美。我觉得我这一生,无论是做人还是从艺,都一直在坚持践行这一点。而且,这一性格及理念的形成,跟我童年的经历息息相关。

我父亲是军人,在部队做文化工作,我的童年几乎就是随军,从一个军营到另一个军营的记忆。那一年,我们家就住在部队俱乐部化装室延伸出的那一趟平房里,睡觉的地方就是剧场的化装室,再开门就直接上舞台了。歌剧“三月三”、话剧“夜闯完达山”、大合唱“英雄战胜了大渡河”、电影“洪湖赤卫队”……小时候耳染目濡了解了很多东西。
童年有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父亲导演的话剧《血债》写日伪时期敌人迫害老百姓的故事,描写一个家庭,男人被敌人抓去做劳工,被害死了。我扮演这个男人的儿子,那一年我9 岁。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剧中父亲的尸体抬进家,我非常投入,大叫一声爸爸就扑上去使劲地哭。演完后下台,父亲批评我,说你演错了。我说没有啊,我当时真的哭了,流了很多眼泪。但父亲告诉我说,那个年代,孩子管自己的父亲叫爹,不叫爸爸。演戏不仅要和真的一样,还要回到当年。这个细节要点我记住了,可第二场演出,我扑上去,爸爸喊了一半儿,觉得错了,就赶紧改口喊爹,所以就哭成了“爸爸——爹”!这件事情我终身难忘。父亲当时对我说,艺术要符合真实生活的。这一点,在我一生艺术创作中影响最深。
当年是如何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启演艺生涯?
当年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完全是机缘巧合。那时我当兵在部队,坐四路电车上街会看到长影大门。一次我上街买牙膏,碰到一个人,他说他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叫王修才,他要了我的联系方式。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人、这件事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后来有一天,我在部队训练扔手榴弹,我还记得那天投掷了47.8 米。连里的文书跑来说长影和团里联系,让我去参加考试,说他们招演员。当时我对这事并不感兴趣,因为我在部队特务连是技术骨干,是军侦察处培养的苗子,我当时的梦想是希望做一个侦察员,在情报战线当英雄。团长知道我不积极,把我叫去训了一顿,说这是任务!不能给军人丢脸。
那年考试的科目,先朗诵了一段文章,唱一首歌,接下来让我跳一段舞。我说不会舞蹈,我说我给你们打一套部队侦察兵的扑俘拳吧……考完试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之后就回连队了。这之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因为一个战友被别人欺负了,我仗义执言替他打抱不平,那时候年轻气壮脾气火暴,犯了错误要受处分。这时正好长影发来通知我被录取,连长张闻海命令我马上去长影报道……于是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长影,进入《山村新人》剧组,出演一个配角,正式开始了演员之路。
1980 年,出演根据鲁迅名著《药》改编的电影,由此成为备受瞩目的新星,这个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在长影厂当演员的那些年,我陆续出演了《血沃中华》《大小伙子》《刀光虎影》《伐木人》等一些电影,基本上都是配角。1980 年出演根据鲁迅的名著改编的电影《药》,这是我进入演员这行戏份最重的一部戏。为了描写革命者夏瑜临死之前的那种从容就义的心态和视死如归的情怀,拍摄时我就设计了他提笔写字,用手把毛笔笔锋上支出的一根毛刺儿拔掉的动作,这个细节我认为能准确反映革命者牺牲前视死如归的心态,导演觉得这个动作设计得非常好。后来这个动作的剧照还刊登在《大众电影》杂志上,有影评人专门撰写影评来分析这一细节。
1982 年出演的影片《心灵深处》,成为演艺生涯的转折点,这个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影片《心灵深处》拍摄于1982 年,到今天已经四十年了。前年父亲节前夕,《心灵深处》导演常彦的女儿常璐璐打电话给我,她说父亲节想送给父亲一个礼物,常彦导演已经90 岁了。常璐璐想让我联系一下刘晓庆,希望刘晓庆拍摄一个视频,她把这个视频当作是父亲节的礼物送给常彦导演,让父亲高兴一下。
我和刘晓庆赶紧联系了,晓庆愉快接受这个提议,并且很快就录了一个视频。我们把视频转给了常彦导演,常彦导演看了视频非常高兴。他还给我回复了一个视频,视频里他还叫了我一声“小伙子”。听到当年恩师的声音,我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常彦导演是我们长影的著名导演,他执导《保密局的枪声》曾经夺下了当年电影票房最高的纪录。我有幸在常彦导演的手下工作,参加了他三部戏的拍摄。拍摄第一部戏是反特片《熊迹》,在这个片子里我演一个小角色,戏份很少。我跟常彦导演合作的第二部戏是《保密局的枪声》,这个戏当年红遍了大江南北,我在戏里面演保密局的特务余云禄。
我跟常彦导演合作的第三部戏就是《心灵深处》,我在片中出演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张森,刘晓庆出演军医欧阳兰。可以说常彦导演是我艺术生涯中的贵人,他邀请我出演《心灵深处》,这个影片后面发生了很多故事,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也影响了我的艺术创作之路,关于《心灵深处》,关于我和刘晓庆,前些年已经有大量的报道和传闻,我也在《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那本书中,用很大篇幅讲述了当年的一些拍摄花絮和幕后故事。可惜现在我手头一本书都没有,都被别人借走拿走了。
我和刘晓庆运作拍摄两部电影
1984 年离开长影,转行做导演,身份的转变,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和心理?
我离开长影,原因其实众所周知,因为拍摄《心灵深处》后,我与刘晓庆的感情纠葛,我受到厂里的批评,也受到外界很多非议。当时,我前妻赵雅珉同意协议离婚,之后我离开长影,来到北京。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应该算是最早的“北漂”吧!晓庆托朋友把我的工作关系暂时挂靠在一所大学,后来又找到朋友巴耀忠帮忙,我的档案转到一个街道办的工厂,当厂长助理。从飘忽不定的无业游民变成了有工作的国家职工,真是不容易,特别感激那些年、那些朋友对我和晓庆的帮忙和照顾。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打算建立一个影视基地,邀请我和刘晓庆加盟,希望我们能从单位离职下海。但当年,我们斟酌再三,还是没有勇气下海。可能是受了当时改革开放气氛的影响,我和晓庆也想乘着改革东风,大展拳脚,创出一番事业,于是就想从本专业入手,决定拍摄一部电影。一方面我可以第一次做导演,另外,我们也可以摸索着为中国电影做一些尝试。
当年拍摄《无情的情人》和《大清炮队》这两部影片,经历了哪些波折?
《无情的情人》和《大清炮队》这两部影片,是我和刘晓庆一起运作拍摄的两部影片,也是我导演生涯里的处女作和最重要的两部作品。
《无情的情人》应该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因为之前只有国家电影制片厂有拍摄权,经费也是国家投资。我拍《无情的情人》的时候,电影界还没有允许社会融资,也没有任何官方文件和先例,于是我和刘晓庆决定自己尝试来拍,也算是电影改革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刘晓庆也创造了另一个第一,当独立制片人。

记得当时晓庆说,改革干别的,咱们不行,拍电影可以。之后,我们开始寻找剧本,晓庆对《无情的情人》这个剧本情有独钟,尤其欣赏女主人公敢爱敢恨的特性。当时,很多人都看好这个故事,在我们之前,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立项立过五次,甚至听说两次已经建组了,但是后来都没有拍成。所以晓庆决定我们就拍《无情的情人》,由晓庆主演。之后我们带着剧本来到广州,深圳找到过市长、找到深圳蛇口工业区袁庚同志、还有香港银都机构许敦乐、还有深圳影业有限公司的郑会立大姐……大家合力相助,可是还要找一个“户口”,我们找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孙长城,孙厂长欣然答应投拍,接下来我和晓庆就开始四处筹钱、找摄影器材、看外景。
影片外景地选在四川阿坝,风景很美,但缺吃少喝高寒缺氧,全组100 多号人只配备一个氧气枕头。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刚开机没几天,就遇到了演员罢演,说起来原因都很简单,就是在外景地拍戏常常吃不上饭,有个剧务偷偷地给一个演员一个鸡蛋,结果别人发现后就不干了。就因为一个鸡蛋引发了停工。面对这个局面,晓庆很干脆,她说,大家如果同心协力,困难不是不能解决,但是如果拿这种事情来要挟罢演,绝对不行!摄制组先停工,临时火速换演员和摄制组人员。
拍《无情的情人》,我是第一次当导演。所以我的压力很大,我之前也没有受过导演的专门学习,只是看了几本导演专业的书,就凭着自己的感觉来拍,甚至拍完了之后,连晓庆都很怀疑,这些镜头能接起来吗?拍出的东西能行吗?另外,当年也出现了资金短缺的局面,晓庆是制片人,她来管资金,拍摄中间费用花光了,她就得赶紧四处再去找钱。记得当时深圳影业有限公司的郑大姐寄来5 万元来结账,全组才能从高原走下来。现在想起这些往事,真是感慨万千。《无情的情人》算是第一部利用社会融资来拍的影片,身为制片人,刘晓庆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界第一个独立制片人。
《无情的情人》影片结尾,有一首男女声对唱插曲,由于资金捉襟见肘,没钱找歌手,我就跟晓庆说你唱吧,她说我行吗?我说你行,你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你没问题。我说男声可以请一个好点儿的男歌手来唱,但晓庆说不,还是你唱吧。就这样,我们合唱了这首吕远老师作曲、我写歌词的电影插曲。由于题材特殊,《无情的情人》命运多舛,当年这部影片前后审查修改了25 遍,晓庆常常急得直哭。当年,法国有关人士很喜欢这部电影,希望我们能报送戛纳电影节,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非常遗憾《无情的情人》与戛纳电影节擦肩而过。
拍完《无情的情人》,我和晓庆就开始筹备我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大清炮队》。《大清炮队》这个剧本呢是为晓庆量身定做的,写了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女扮男装上战场,和外国侵略者战斗的故事。《大清炮队》公映的时候引起轰动,报纸上对这个电影的评价很高,因为很多清朝的戏都把注意力放在后宫争斗,而《大清炮队》另辟蹊径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特别是影片最后一个冒名顶替上战场的女兵挺着长矛,骑着马和敌人同归于尽,这是电影史上没有的视角,是通过写实的手法表达写意的作品,所以很新颖。
拍电视剧偿还拍电影欠的账
您执导的电视连续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曾轰动一时,当年如何从电影导演转变成电视剧导演?
首先说,电影导演变成电视剧导演,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用视听语言来讲故事。我后来的创作,跟我个人的生活有关。那几年,我的生活经历了婚变,还弄了几年官司,这个事情当时很轰动,大家都知道。我还写了一本书《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当年我独身一人,面对很多社会压力,有很多人认为我不适合做导演,之所以拍了两部戏,那是因为刘晓庆的关系。当时,听到这些很生气,就想继续拍片用作品证明自己的能力。那时,正好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办了一个三年制的学习班,每天晚上可以去上课,所以我就参加了全国成人高考,考到这个班开始系统学习理论知识。
上学期间,我拍摄了喜剧片《宝贝小偷与大盗》,是一部反腐题材的戏。后来,由于这部影片题材敏感,拷贝发行上受到限制。《宝贝小偷与大盗》之后,我又拍摄了《慰安妇七十四分队》,之所以要拍摄这个敏感的题材,我觉得自己身为电影人,要提醒后人勿忘历史。这部电影也是因为题材原因,后来结果不佳。当时真是伤心啊,四处筹措的资金,这个影片的一半资金是我借朋友的,连同编剧的稿费和我个人的酬金加在一起,作为影片的投资,结果付之东流。
做导演那几年,我拍的这几部戏都波折不断命运多舛。所以说为什么从电影导演变成了拍电视剧的导演呢,因为没钱啊,我得赚钱还债啊!
那时候写《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其实背后也有隐情。离婚的时候,我和晓庆有个约定,大家都分开了,希望不伤害彼此,对于我们俩婚恋的事情,大家都对外不谈为好。她当时也答应了,但后来她那边出了一本书叫《亿万富姐》,涉及到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也是没办法了,既然你先违反承诺,那么我也可以写。
其实开始写书的时侯,我仍旧犹豫……后来,朋友的一番话解开了我的困惑,他说你们俩的故事还会被继续炒作下去,过些年呢,你们都不在了,可是你的后人还活在世上,你们的故事不能任由以后的人去任意改写,这也算是给后人一个交代吧。朋友的点拨,使我一下子释然了。另一方面,我当时负债巨大,拍一集电视剧酬金就几百块钱,远远无法还清欠朋友的钱。那时候还真有这点儿私心,得赶紧赚钱还债。就这样我写了《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用这本书的稿费,把我拍摄电影欠的账总算还上了。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电影是我钟爱的。但当时的境遇,我改去拍电视剧,也是无奈之举,人总要生存要生活啊,后来我就在很多人眼里成了电视剧导演。
我当电视剧的导演,依旧是用电影导演的电影语言来拍摄电视剧,这也是为什么《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剧中李琳扮演的女主角山杏获得了全国观众的认可,获得了当年的飞天奖。

近些年来,您先后拍摄了《末路》《威胁》《国家命脉》《大潮如歌》《潜龙道》等电视剧,这一段时间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事?
说起来有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不知道电视连续剧《末路》是我拍的。当时片子拍完后,片头字幕的人员名字特别多,都想挤占片头,结果我一生气,片头位置我就不跟你们挤了,我把自己的名字放到片尾。但播放的时候,没想到电视台把片尾字幕剪掉改播广告,结果很多人就不知道导演是谁了。《末路》这部刑侦剧当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南京的朋友告诉我,放《末路》的时候街上都打不到出租车,司机都回家看电视剧去了。
电视剧《威胁》描写的是矿难的故事,之所以拍这个题材,跟我的经历有关。我当兵第一年部队学工学农,我们特务连去吉林的辽源挖煤。那回发生井下塌方,我的班长张国元同志牺牲了。还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井下值班。那天雨下的特别大,我怕电机被淹,从井下爬上来,刚刚爬上井口,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转头望去,矿井巳经被水灌满了!如果我晚上来5 秒,那年我就死在那里了!了解我的朋友和熟悉我作品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我特别钟情于拍摄一些现实题材和敏感题材的作品,因为我觉得,文艺工作者应该肩负社会使命,作品和生活应该息息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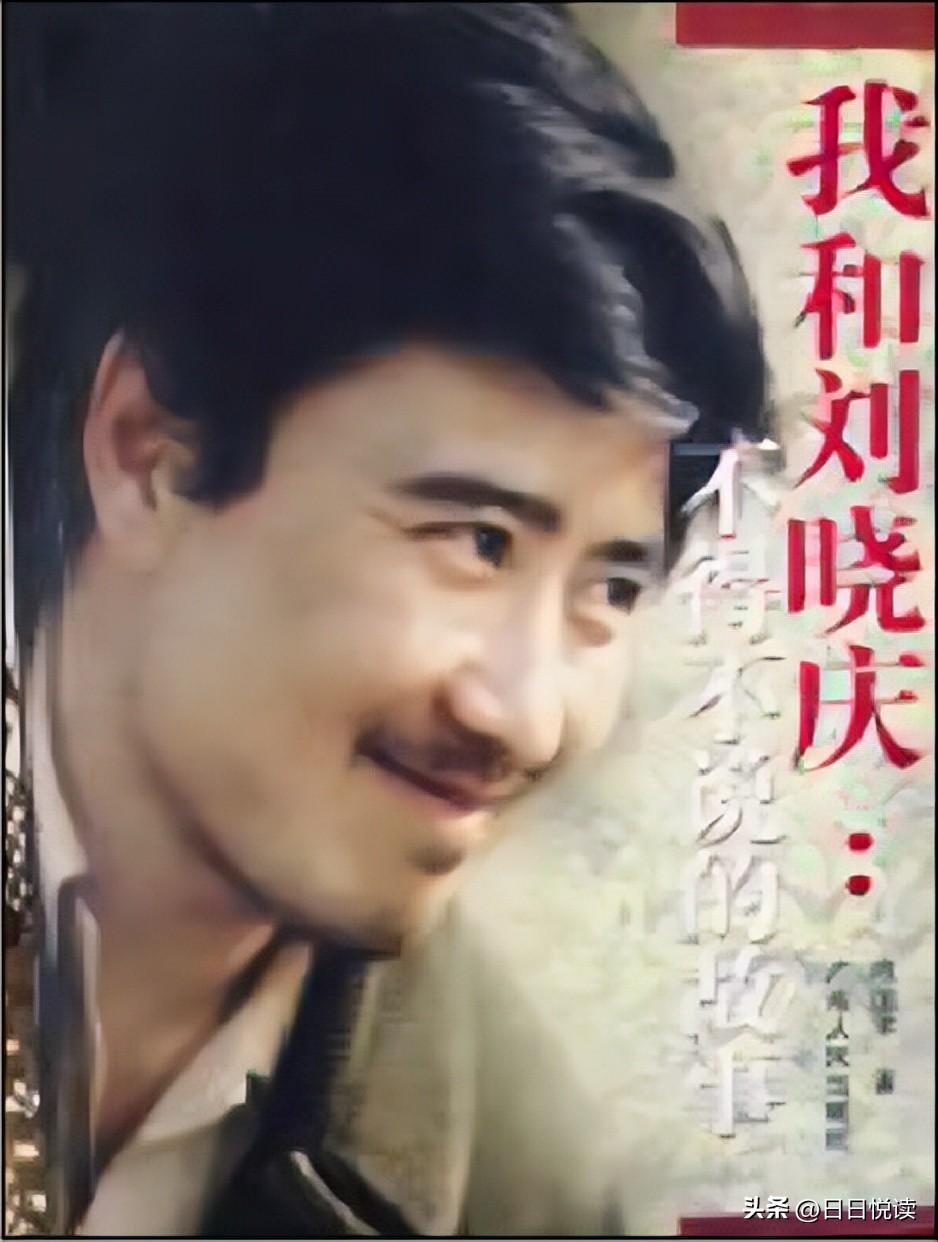
平和看待对我的误解和误读
您与刘晓庆的故事曾广受瞩目,是否存在误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关于我和刘晓庆的话题,一直以来我很反感也很无奈。最反感的是,很多人在介绍我的时候,常常冠以“刘晓庆前夫”的头衔儿。其实我很不愿意谈我们的事,在我看来和刘晓庆许多事是两个人的私事,而且巳经过了近四十年。遗憾的是很多人仍然还是对这个“前夫”称呼感兴趣,好像是说我也跟着借了“前夫”的光!
我和刘晓庆的一段婚姻,虽然发生了许多故事,但毕竟已经是过去时了。现在很多人仍然乐此不疲谈论这些事情,甚至只关注这件事情。前几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有个学术活动,放了我导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然后有媒体对我进行了一个简短采访。结果最近我看电视,还是称我为“刘晓庆前夫”,还是谈论我和刘晓庆的往事,而且还咬牙切齿贬损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现实就是这么个状态,看到这些,我真是很无奈。
我和刘晓庆,那是一段风风雨雨的故事,实实在在都已经过去。其实和她分手之后,我拍了许多的电视剧,而且这些电视剧都受到了人们的好评,我有我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艺术上我也有我自己的成绩,但很多人不会再说陈国军不会当导演,只是说他因为刘晓庆才当了导演。我不否认在我转行做导演的过程中,晓庆有很多的帮助。但我们解除婚姻后,我继续拍电影拍电视剧,都没有受到过晓庆的帮助,我早就用自己的作品已经证明了,我是一个称职的导演。
我与刘晓庆的故事,世人注定会有误读和误解。其实换句话说,凡是文艺作品,发表之后,世人的评判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年,我们两个人都出版了书。我那本书其实写得非常潦草,而且很快,20 多天就写完了。当时正在拍电视连续剧,每天应付大量的拍摄任务。
另外,世人在炒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记得当年我们闹离婚的时候,有一次在火车卧铺车厢,看到一个青艺的年轻演员,跟周围的人说我的“故事”,他说陈国军这个人非常彪悍,身上永远带着一把蒙古匕首,喝酒一顿起码喝二斤……他说得很起劲,周围的人也听得很来劲。后来我实在按捺不住,我故意凑到他跟前,他根本就不认识我。过了一会儿,大家散开各自吃饭了,我就把他叫到火车车厢连接处,掏出我北影的工作证,我说你看我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陈国军。
他一看,马上很不好意思,连连小声的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陈国军老哥……当时场面真是令人哭笑不得。这种事情我经历过多次,误读和误解总是有。身为公众人物,观众愿意怎么去理解就怎么理解吧,我都可以接受,哪怕批判也没关系。当年我那本书出版之后,全国各地来信像雪片一样,都用麻袋装回来。我一封都不看,因为我没有时间回信,我也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再去纠缠解释,因为已经过去了!
演艺生涯中,刘晓庆是一个常被提及的名字,您如何评价刘晓庆?
说实话,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因为不管如何评价,都是不准确的。我觉得晓庆是个非常睿智的人,她非常聪明,比一般人聪明得多,有时比我聪明得多。晓庆是多面的,也是立体的。赞扬她呢,有很多的例子。批评她呢,也能找出很多事情。生活中,她是个非常好的人,当年我母亲来北京看病,她陪我母亲去医院,还带她去长城游览。那时,她做得非常到位,做得非常好。这一点来说,我很感谢她。在我们拍第一电影《无情的情人》的时候,我亲眼见证她如何成为中国第一个独立制片人,她为了把他心爱的人扶上导演的位置,使尽了千般力,受尽万般苦,那种情真意切我能深深感觉到。这种对我的好,或者说对我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当年我们为了拍片筹钱,一起演出到处走穴,常常吃住都在后台,一天演九场,这边卸完妆就上车赶往下一个演出地,在车上一坐就是一夜,真是吃尽了苦头。那时正是创业阶段,两人风风雨雨,一起吃苦,互相照应,真的有许许多多让人感动让人不能忘怀的故事。这些故事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想起来依然恍如昨天。所以我怎么评价她,用什么赞美的词句都不为过。回忆当年她的付出,我不能讲假话,即使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是这些好,永远在我心里最深处珍藏着。当然,晓庆身上也有她的问题。我也不必回避,因为只有这样来说,才是一个真正的她。我觉得做人还是要厚道一点,夫妻不成成仇人,我不赞成这样。非要我评价她,我要客观的说,晓庆是善良的人,这一点足够了。
从当年写书到如今旧事重提,心态有何变化?近些年来,您与刘晓庆曾一起录制电视访谈节目,这一过程中有哪些趣事?
我30 年前写《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的时候,当时的心境和30 年后是不一样的。如今再平静看陈年往事,即便还有鲜为人知的故事,虽然旧事重提可能会满足读者的阅读心理,但我还是不打算再说什么了。虽然我们不是夫妻了,但起码还是好朋友,不能老借往事来做抵押。朋友之间老是纠缠旧事,也显得不厚道。至于你问,那当年你为什么要写呢?而且写了50 万字,而且在你和刘晓庆的官司当中,双方都咄咄逼人。难道现在改变主意了?现在说起来,应该说是改变主意了。现在已经不是当前的彼此了,大家今天依然是好朋友,好朋友就不能总在往事上纠缠不清。况且这次回想起许多当年的好,对于35 年后的我足够了。
接受你的采访,我不打算说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但当年之所以在离婚官司上不依不饶,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一方面是当年年轻气盛,不能接受上级某些人强行干涉我们的婚姻。
外界干预打压,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判断。另一方面,在起诉书上,说我有家暴问题,这个我不能接受!我从来没有打过刘晓庆,这句话我可以负法律责任。
前几年河北电视台做一个刘晓庆的访谈节目,节目组邀请我参加。我答应参加录制时,他们把脚本给我看,上面在介绍我出场时,用的介绍语是“一个向你道歉的人”,看到这个,当时我就不同意,我说我需要向她道歉什么呢?节目组说你是不是应该就书里写的有些内容向她道歉呢?我说我写的都是实事求是的,虽然没有什么高的文学水平,但却是实话实说。
我跟节目组说,不能这样介绍我,这样介绍不妥,因为我来参加节目,不是来向她道歉的。后来节目组问我,那以什么名义说呢?我说你就说,我是“一个他最恨的老朋友”。最后在节目当中,主持人也这样说了,把前面那个“我是来道歉”的话删掉了。后来在录制节目当中,晓庆对我说:“你向我道歉。”我觉得很诧异。我说:“我道歉什么?”她说:“你写了那本书,你应该向我道歉。”我当时很认真地问她:“晓庆,我那本书哪个地方写的不对?你告诉我,如果是真的有错误,我向你道歉。”
后来她说她没看过这本书,我说你都没看,你怎么让我向你道歉?我哪些地方撒了谎?哪些地方说的不对?后来晓庆说:“不行,你一定向我道歉,这本书对我造成了伤害。”我当时讲,因为两个人各自写的书,不可能完全客观全面,两个人站的角度不同。另外,走到离婚这一步,两个人都有错,离婚双方都有责任。我身上也有错误,我在写的时候肯定会加重了个人的感受,难免会有有失偏颇的地方,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向你道歉。
节目现场就是这么说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节目播出的时候,他们只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向你道歉。前面我跟刘晓庆的那番对话和我道歉的本意全都被剪掉了。节目播出后,很多朋友都质问我:“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还道歉了呢?”听到朋友的指责,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我当时不是这个意思,但播出时我说的话被剪掉了。哎呀,一声叹息,经过剪辑的东西,其实和现场发生的是不一样的,但现实就是这样,后来我也渐渐释然,我说道歉就道歉吧。
近年来,有许多关于您的娱乐报道,在您看来有哪些误解和谣传?
这么多年来,许多文章都存在误解和谣传。有幸被当作公众人物,我能理解,我的态度也是不去置评,也不想去纠缠。有些事情就是这样,会以讹传讹。倒是有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做澄清,就是有很多媒体报道称,当年晓庆拍戏,我去现场大闹,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我觉得这个误传的源头应该源于两个非常著名的导演,一个是谢晋导演,另一个是李翰祥导演。
我与谢晋导演见过一面,那是在湖南湘西王村,当时我在珠影剪完《大清炮队》,去《芙蓉镇》剧组探班。晓庆带我去谢导的房间看样片,谢晋还很客气地征求我的意见,说你也是做导演的,你给提点儿意见。我当时也是年轻,也是真傻,不知道人家本来是想听称赞的话,于是我就照直说我的观感,提了几点意见,说了几句实话。当时谢晋很不快,对我的意见也很不以为然,这个我能感觉到。后来晓庆埋怨我说,你怎么搞的,不会说几句好话吗?我说我觉得我也是做导演的,他既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以诚相告又有什么错呢?
这一次是我跟谢晋导演的唯一一次见面,也许是我的态度引起了他的不悦,后来我跟晓庆婚变,谢晋导演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陈国军到上影厂的摄影棚大闹,影响晓庆拍戏,影响她进入角色等等。我当时看了十分诧异,因为这是无中生有。我从来没有进过上影厂的摄影棚,怎么可能说我去上海摄影棚里闹事儿呢?!谢晋这篇文章里边的不实成分,被后来很多文章转载延用。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李翰祥导演在广东的报纸上,也谈到我去他的拍摄现场闹事儿,那时应该是他拍《一代妖后》,文章里他说在现场曾严厉地制止和批评我。我看了这个无中生有的报道真是无语,我根本就没有到过李翰祥的拍摄现场!
李翰祥导演对于晓庆的成长道路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因为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把晓庆介绍到了海外,我对这两部戏很欣赏,我对李翰祥导演也很敬重,但是李导演在报上公开说这种没有的事情,这让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想申辩什么了。如今谢晋导演和李翰祥导演都已经作古,我想有些事情我再不澄清一下,那么他们留下的那些不实的报道就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所以,今天我在这里真是不成敬意,两位导演对不起啦,我只能说明一下,我从来就没有去过你们的片场闹过事儿!

我现在的家庭生活和睦温馨
如今很多读者非常关注您的家庭生活,您有什么故事和大家分享?
我现在的家庭生活很好,和睦温馨,平静充实。我现在的妻子叫傅丽云,她小我16 岁,曾经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拍过很多知名的广告。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第一段婚姻和长影演员赵雅珉生的孩子,他叫陈赫,加拿大留学回来后他也进入导演这行,跟着著名导演郭宝昌学习拍戏,担任执行导演,郭导对他称赞有加。大儿子跟我一起也联合拍了几部电视剧,《松花江上》和《潜龙道》都是我们联合执导的。他自己也独立拍了几部戏,也写了几个电影剧本,很努力。我二儿子陈永林是我和妻子傅丽云所生的孩子。二儿子喜欢足球,上中学了,是学校足球队的成员。
如今是新媒体时代,经常会遇到媒体人采访我,经常会问到往事,尤其是我在电视节目里多次谈到刘晓庆,对刘晓庆赞誉有加,换位思考,这些语言对生活会带来一些些困扰……在这里,我要对我现在的妻子傅丽云表示谢意,感谢她的理解和包容!我很多话有时候难免会被外界误解,我要借这个机会向妻子傅丽云表示歉意。
您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的艺术人生?
我是导演中唯一一个侦察兵出身的导演,我心里始终珍视这份侦察兵的荣耀!军人出身,我始终有一种使命感。回想自己的艺术人生,我觉得最成功的一点就是诚恳诚实。我的作品不说假话,不去粉饰生活,不去违心讨好,而是关注弱势群体,关心普通人的命运。我始终觉得,做人要诚实,要敢说真话,我努力做到了。
评价自己的艺术人生,有很多的标准,比如说作品是不是受广大观众的喜欢,这个我还是很欣慰的,有作品能得到观众认可,创造过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我已经很知足了。还有一个评分标准,就是得奖,我的作品得了两次飞天奖,也得过五个一工程奖和华表奖,也应该算成功了。
如今,我并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还在筹备影视剧的拍摄。平时我也没有停下笔墨,还在写剧本。永不停步,奋斗终生,这是我的一个座右铭。导演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退休,我依旧要拿出满意的作品奉献给观众。目前,我筹拍的几个戏都在筹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