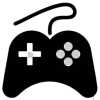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晚年写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Nomoi)里,通过其中三位对话者的交流与讨论,柏拉图思考如何建立“次好城邦”。相比于在《理想国》(Politeia)里柏拉图构建的最理想城邦,《法律篇》着重于更实际的“次好城邦”。当谈到音乐在建立良好政体中的作用时,作为其中一位对话者,雅典异乡人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姿态怀念了在旧时,民众的音乐由贵族长老指定,音乐的作用在于陶冶灵魂及塑造城邦公民品性,哀叹在当下,音乐成为了艺人们满足大众趣味之物。特别是,为了不断满足民众追求新奇感的需要,艺人们不断混音,制造出“不雅”之乐。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柏拉图在《法律篇》里构建了一个词:“剧院统治”(theatrocracy),以表现流行音乐对公民生活的统治。柏拉图在《法律篇》里对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希腊商品化、大众化的音乐的批判可以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流行音乐批评的开端。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的音乐评论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到民众的对立面:民众喜欢的文化肯定是有问题的文化,而知识分子则通过构建理想化的过去,来表明当下民众的喜好为什么是有问题的, 以此间接衬托自己是有正确喜好的文化人,暗示自己拥有比普通民众更高的文化品味。

柏拉图
如果说柏拉图强调在音乐商品化生产机制下,艺人通过混音来满足民众口味的话,在21世纪的社交媒体时代,存在一种混音极其厉害、无比商品化和高度产业化的音乐:韩国偶像流行音乐或者全球粉丝口里的K-pop。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柏拉图如果在世,一定不会放过对K-pop进行批判的机会。1987年,美国著名保守派思想家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1930-1992)出版了《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对美国大学生及青年文化进行了分析与批判。在批判美国大学生和年轻人沉迷于摇滚乐时,布鲁姆就引用了柏拉图的流行音乐批判作为学理支撑。
2012年,不时为美国各媒体撰文的著名评论人约翰·塞布鲁克(John Seabrook)在《纽约客》上发表“工厂女孩:文化技术与制造K-pop”(Factory Girls: 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Making of K-pop)一文,对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的K-pop现象进行介绍,毫不客气地把韩流偶像称为工厂女孩,并且称某著名二代团成员只是二流歌手,发问为什么这个团的演唱会在美国会有人看。尽管塞布鲁克的文章只是媒体文章,他的“工厂女孩”隐喻在2018年成为一本叫《从工厂女孩到韩流女星:韩国流行音乐产业发展主义、父权制与新自由资本主义里的文化政治》(From Factory Girls to K-Pop Idol Girls: Cultural Politics of Developmentalism, Patriarchy, and Neoliberalism in South Korea's Popular Music Industry)的学术专著的标题一部分,这本书的作者是任教于宾州切尼大学的金久用(Gooyoung Kim)。在书里,金久用毫不客气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下,结合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与大卫·哈维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批评,在韩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外向型发展经济的视野下,对K-pop产业进行了犀利分析与本质性批判。如果说像布鲁姆继承柏拉图的流行音乐批判那样,仅仅去批判在社交媒体时代下青少年不读书沉迷流行音乐在学理上已经站不住脚的话,如金久用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的对流行音乐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路径,则显得更加犀利。这也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里一直存在的一个反讽现象,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很多持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者的文化品味却是非常保守的。在热衷于揭露流行音乐和文化的资本主义属性时,对于古典音乐、戏剧与芭蕾舞这样的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这些学者的接受度却要高得多。从这个角度而言,至少在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和布鲁姆一样,都是柏拉图的继承人。

《美国精神的封闭》
当然,随着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的高度发展,对流行文化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批评更多只是研究中的一个视角,而非目的本身。因此,至少在英语学术界关于K-pop的研究里,金久用的路子并不是主流。相反,在承认K-pop是一种高度产业化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前提下,学者们更倾向于以了解而同情的姿态,对K-pop各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细节探讨。刚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K-pop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pop)可以说能代表这一更主流的研究路径。该书主编金淑荣(Suk-Young Kim)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戏剧、电影与电视学院的表演研究教授,也是现在北美韩流研究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相对于很多当代东亚文化研究者,金淑荣有非常独特的学术背景。她并非一开始就是东亚研究出身,而是俄罗斯文学出身,她在2001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关于果戈里记载的乌克兰故事。后又于2005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对1960、70年代中国和朝鲜电影的比较研究。金淑荣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是关于当代朝鲜的传统表演文化。而她的第二本专著关注的是媒体与艺术对朝韩边境的呈现。相比于前两本书,金淑荣在2018年出版的第三本书,《韩流现场:粉丝、偶像与多媒体表演》(K-pop Live: Fans, Idols, and Multimedia Performance),成为了她目前为止最著名的书。这本书对作为一种媒体文化的K-pop表演里的虚拟性和现场性的辩证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成为英语学界K-pop研究里的必读著作。因此,金淑荣同时拥有俄罗斯研究、中国研究、朝鲜研究和韩国研究四重背景,这在学术界极其少见。当然,相比于2018年,现在的韩流产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都在《剑桥K-pop指南》里有所体现。

《剑桥K-pop指南》
在前言“舞台灯光下的韩国时刻”里, 主编金淑荣简明扼要对K-pop及其背后机制进行讨论,尤其对什么是K-pop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首先,金淑荣认为K-pop既是韩国人的民族骄傲也是全球亚洲群体新的族群认同的来源;而对于西方的批评者而言,K-pop再次验证了西方人对亚洲人的偏见,K-pop偶像符合西方人头脑中关于亚洲人没有创造力、只会完成机械完成任务的刻板印象;而对于热情的粉丝们,K-pop则是新的群体建构的方式。其次,就K-pop里的K,金淑荣强调,K-pop可以代表“键盘流行文化” (keyboard/keypad pop),以强调K-pop作为一种社交媒体文化;K-pop可以代表“抽纸巾流行文化”(Kleenex pop),以表现K-pop作为一种更新换代极快的流行文化,大家消费K-pop就像使用抽纸巾一样;K-pop也可以被称作“番茄酱流行文化”(ketchup pop),以指出K-pop的工业性,大家消费的K-pop像番茄酱一样是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就K-pop里的pop,金淑荣也同样从K-pop的表演性(performative)、图像性(picturesque)、大众性(populace)三个方面进行讨论。结合K-pop融合很多音乐和舞蹈传统的角度,强调社交媒体时代下K-pop展示的音乐力量。而在接下来,金淑荣特别强调社交媒体对流行音乐产业的改变,指出K-pop在全球的上升其实和流行音乐的社交媒体转型是同步的。
在金淑荣提纲挈领的前言之后是第一部分“谱系”,包含两篇文章。首先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长于传统韩国民歌研究、同时兼及早期韩流历史研究的罗尔德·马里昂凯(Roald Maliangkay)写的“靠着这个男人:韩国流行音乐的早期新自由主义”。这篇文章从当下流行音乐研究(尤其K-pop研究里)的新自由主义批评出发,强调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即强调自我营销与人设塑造),在20世纪早期的韩国流行音乐中已经出现。马里昂凯认为,作为当代K-pop特点的粉丝文化、选秀造星,在 20世纪30年代的韩国流行音乐已经有所表现,而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作为现代音乐产业特点的唱片公司与广播电台则是这一早期新自由主义文化的经济基础。马里昂凯也特别注意到,早期选秀平台也为日本统治下的韩国艺人们走出国门,展现韩国主体性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马里昂凯还关注了韩国在独立后早期(即1950年代与60年代),由于威权政府管制,韩国艺人在缺少之前的广播平台的情况下, 为驻韩美军表演成为了很多艺人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出现了1960年代闯美成功的金氏姐妹花(The Kim Sisters),开创了韩国艺人赴美表演的先河。

金氏姐妹花
接下来的章节是由韩国圣公会大学研究东亚流行音乐的申贤俊(Hyunjoon Shin,音译)所写,这一章“梨泰院Class、江南Style与汝矣岛明星”关注1990年代的韩国流行音乐历史。与一般仅仅关注徐太志与孩子们以及三大娱乐公司早期历史的叙事不同,申贤俊摆脱了后见之明去书写早期韩流历史。在讨论90年代韩国经纪公司兴起及广播公司对音乐垄断地位消失的背景下,申贤俊强调了90年代韩国流行音乐的一大特点是以梨泰院为代表的地下文化与经纪公司结合的开始,即梨泰院地区拥抱嘻哈文化的地下DJ、舞者们希望更走向主流,而李秀满则也希望向韩国推介包括嘻哈在内的欧美流行文化,而SM的早期艺人组合玄振英与WAWA是这一合作的代表。当然,正如申贤俊强调,到后来SM更多走日系路线,有了BoA及H.O.T.这样的一代偶像。接下来,申贤俊介绍了创造了90年代韩国流行音乐上千万销量的两名艺人:申昇勋与金建模,而他们都来自Line公司。申贤俊特别强调,该公司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混合性,并对电子音乐下的音乐混合进行了反思。在这样的情况下,申贤俊才介绍了更为一般韩流历史强调的徐太志与孩子们。
可以说马里昂凯与申贤俊的这两章互相补充,为读者了解K-pop兴起前的韩国流行音乐历史提供了清晰的图景。特别是申贤俊在结尾特别反思了韩国流行音乐里的成王败寇的现象,而他这一章恰恰是去挖掘那些没有进入粉丝知识体系的K-pop历史中的那些早期先行者。在这两章对历史进行了概括后,接下来进入专题部分。第一个部分“视听K-pop”分两章。第一章是由杜克大学研究现当代韩国音乐的李郑闵(Jung-min Mina Lee,音译)写的“寻找K-pop里的K:风格历史”。从K-pop是否能构成一种音乐体裁的角度的问题出发,李郑闵强调构成K-pop独特风格的不在其音乐形式,而在其生产方式。以这个角度为基础,李郑闵将K-pop风格分成三个阶段:最初阶段,1996到2006年;第二阶段,2007到2017年;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在第一阶段,K-pop主要是亚洲现象,以偶像音乐为特征的K-pop风格开始出现,在这个框架下,K-pop开始对蓝调、舞蹈音乐、嘻哈音乐等欧美音乐进行吸收。在第二阶段,K-pop开始走向西方。李郑闵强调,英语歌词在这一阶段开始在K-pop呈规模出现,韩国的娱乐公司也开始与欧美制作人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钩子”(hook)与混合两大特征在K-pop里出现,而这两个特征都旨在为K-pop变得更容易被全球听众接受而服务。李郑闵也特别指出,作为一个新兴的音乐产业,K-pop也为欧美的制作人实验新的音乐风格提供了一个平台。而第三个阶段则是K-pop成为全球现象,K-pop的全球音乐生产体系也走向成熟,李郑闵特别指出,当K-pop早期需要为亚洲以外观众接受的情况下,很少有歌曲融入传统韩国音乐特征,但是当K-pop已经成为全球现象时,越来越多的K-pop歌曲融入韩国传统音乐元素,作者强调,防弹少年团的成员闵玧其以Agusta D发布的单人说唱曲《大吹打》(Daechwita)是融合传统韩国音乐最好也最大胆的一首。

《大吹打》里闵玧其吸收美国说唱音乐里喜欢吹嘘的方式,把自己塑造为朝鲜王朝的国王
如果说李郑闵的这一章是音乐产业视角下的音乐风格分析,下一章由肯尼索州立大学研究韩国表演文化的金慧媛(Hye Won Kim,音译)写的“记录K-pop的听觉版图”则借鉴了时下文学文化研究里的“声音研究”(sound studies)对K-pop的音乐生产进行分析。以TWICE在2019年的歌曲“PSYCHO”的备忘录版本为例,金慧媛强调音乐里的声音生产作为一个分析对象的价值,特别是在传统以视觉为中心的西方知识论的情况下,声音研究可以强调像听觉这样的非视觉文化的主体性。就K-pop现在以视觉为中心的特点而言,金慧媛认为这是K-pop在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而非K-pop一开始的特征。在这样的关怀下,金慧媛也指出,K-pop不应该局限于男团女团这样的表演者,而应该包括音乐生产后台的流行音乐家们,是这些音乐家创造了K-pop的听觉版图。接下来,金慧媛通过五个由早到近的案例,结合对相关制作人的采访,对K-pop听觉世界的生产进行了分析,特别强调K-pop经历了传统流行音乐的以听觉为中心的转变到现在以视觉为中心的转变,而这一转变过程是与技术演变分不开的,当像MP3等播放器使K-pop音乐变得更容易获得时,韩流产业开始发展视觉文化,以保证粉丝们不满足于只听K-pop歌曲。在金慧媛对K-pop音乐生产的幕后分析里,也强调了音乐家们自己的音乐追求与韩流产业需要之间的张力,比如作者在采访GOT7《Not by the Moon》的歌曲制作人之一艾萨克·韩(Issac Han)时,艾萨克·韩提到了JYP公司的主管朴轸永会对写好的歌曲进行改编,以适合偶像表演需要。

《PSYCHO》一歌的音乐制作人之一EJAE
音乐之后的专题是舞蹈,同样由两章组成。首先是致力于韩舞研究的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吴周妍(Chuyun Oh)写的“K-pop音乐视频编舞”。如果说金慧媛在上一章指出K-pop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听觉向视觉的转变的话,吴周妍则根据现在K-pop的特征,强调K-pop是由偶像舞蹈推动的一种音乐体裁。吴周妍强调韩舞两个特点。首先,韩舞是全球当代年轻人的社交舞蹈。就这一方面,吴周妍强调了粉丝们模范视频里的舞蹈动作与偶像打扮穿着的韩舞翻跳。二是韩舞本身最主要的特征是“亮点编舞”(point choreography),即在副歌里加入短和标志性动作,以表现整首歌的主题与概念。而这一“亮点编舞”特征又让韩舞编舞易于为粉丝掌握而服务。与此同时,吴周妍指出,韩舞在欧美语境下也成为了一种亚洲亚裔舞蹈。接下来,吴周妍根据K-pop音乐常见主题,分清纯型、狂野型、舞蹈中心型、实验型四个方面,对近几年来有代表性的男团、女团舞蹈视频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既包括EXO、Girls’ Generation等二三代团,也包括防弹少年团、BLACKPINK、TWICE等现在大火的团。
与吴周妍更着眼于对韩舞全面介绍不同,接下来瑞利智(CedarBough Saeji)的文章专注于韩舞翻跳。任教于釜山国立大学的瑞利智主攻传统韩国表演戏剧研究,也兼及K-pop研究,尤其是韩舞翻跳研究。在“通过韩舞翻跳实践身体化K-pop热门歌曲”这一章里,瑞利智基于她从2010年开始在网络上追踪韩舞翻跳团体视频的经历,结合现实采访、舞蹈工作室学习、韩舞比赛裁判的经历,对翻跳者的动机、收获以及韩国在背后的支持进行了系统介绍。瑞利智强调,翻跳为K-pop粉丝聚集并集体表达对相关偶像团与歌曲的喜爱提供了机会。通过对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个著名翻跳团体EAST2WEST的一名成员的深度采访,瑞丽智表明,年轻人在专业选择、职业训练上也会受到韩舞翻跳经历的影响。同时,对于北美的亚裔,瑞利智强调韩舞翻跳也为他(她)们探索亚裔群体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提供了机会。在此之外,瑞利智特别研究了韩舞翻跳与性少数群体认同表达的问题,也关注了一些韩舞翻跳者成为练习生甚至成为偶像的问题。最后,瑞利智介绍了韩流产业以及韩国政府在推动韩舞翻跳发展中作用的问题。

温哥华EAST2WEST翻跳团
舞蹈之后的专题是“偶像的形成”。首先是由纽约大学研究民族音乐学与韩流的斯蒂芬妮·崔(Stephanie Choi)写的“韩流偶像:媒体商品、情感劳工与文化资本家”。崔的博士论文是基于她和一些韩流产业的经纪人的联系,得以采访了数家公司的偶像,而这一章则介绍了崔的博士论文里的部分研究成果。在一开始,针对西方媒体长期存在的针对K-pop偶像是韩流工业制造的机器人的想法,崔一方面指出欧美的音乐产业在音乐人“真实”、“独立”的幌子背后有同样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崔也强调,与其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去对韩流产业进行上纲上线式的批判,不如进入韩流产业去进行自下而上式的调查。因此,在对经纪人、音乐教师、偶像本人的采访的基础上,崔对韩流产业从偶像生产、政府政策、偶像内部关系、偶像在音乐生产中的作用、粉丝管理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尽管崔的调查呈现的图景仍然不可避免地体现出韩流是一个从偶像生产到粉丝消费都高度工业化的文化经济产业,但这一章独到之处在于崔对韩流产业的经纪人、偶像进行了真正的采访,并强调作为特殊商品和产品的偶像在韩流产业中不是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如果说崔的章节关注的是标准的K-pop偶像,接下来的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韩国表演与整容业的李苏琳(So-Rim Lee,音译)写的“从K-pop到Z-pop:泛亚洲偶像的生产、消费与流通”则关注了一群在K-pop影响下的非传统偶像:在2019年出道的一个由来自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成员组成的女团Z-Girls。根据李苏琳的介绍,这个团尽管是按照韩流标准进行生产,其制作人在韩流产业也有很高的地位,但韩国观众和媒体对这个团并不接受,特别是因为她们的歌不是用韩语唱的。基于这个情况,李苏琳提出,Z-Girls现象让人们思考当K-pop已经形成某种文化霸权的情况下,K-pop的边界在哪,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被看作是韩流偶像、而什么样的人没有资格的问题。李苏琳强调,Z-Girls现象揭示了K-pop在作为一种全球文化现象和作为韩国的民族产业之间的矛盾。因此,李苏琳特别反思,K-pop一方面代表着作为新兴国家韩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全球文化霸权面前代表着某种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挑战;但在东南亚,K-pop又代表着文化霸权。李苏琳进而认为,韩国观众对Z-Girls的不接受背后是韩国人对作为第三世界的东南亚的刻板印象,东南亚成为韩国人眼里的他者,东南亚人与印度人无法符合“韩流视觉性”(K-pop visuality)下的审美霸权。因此,就韩国通过K-pop对全球进行文化输出这一问题,李苏琳认为其内在逻辑仍然是美国式的种族资本主义,只是代表这一种族资本主义审美的人群由白人变成像韩流偶像一样的韩国人,而Z-Girls对泛亚洲的强调又在挑战着这一新的霸权审美与种族想象。

Z-Girls团体
接下来的部分“震撼世界的团体”则专注于防弹少年团。首先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韩国电影专家金暻铉(Kyung Hyun Kim)写的“防弹少年团、跨媒介与嘻哈”。这一章运用了媒体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跨媒介”(transmedia)概念对以防弹少年团为代表的韩流对嘻哈文化的接受进行了反思。金暻铉在关于欧洲白人对黑人嘻哈文化挪用的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强调包括韩国人在内的非黑人群体对嘻哈文化的采纳会存在与嘻哈社会文化精神脱节的可能性。金暻铉特别关注了2014年Mnet拍摄的记录防弹七名成员在洛杉矶学习嘻哈文化的真人秀节目《美国喧嚣生活》(American Hustle Life)。金暻铉认为,这档节目表现了这个出道时自称嘻哈偶像团却不怎么懂黑人嘻哈文化的自嘲。这一自嘲不仅表现了美国嘻哈与K-pop的区别,也展示了韩国人缺少对美国种族关系切身体验情况下接受嘻哈文化的困境。不过,在另一方面,金暻铉对防弹的活动平台防弹宇宙及防弹粉丝组织阿米也从嘻哈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反观,强调与说唱音乐视频里展现的美国贫民窟生活困境相比,防弹宇宙展现的图景是后民族及后创伤的。最后,金暻铉强调,K-pop无疑展现了说唱能力,但K-pop是否能把韩国这样一个从朝鲜战争里诞生的民族国家背后的真正创伤用说唱形式表现出来,还需拭目以待。

《美国喧嚣生活》里展现的防弹成员在洛杉矶与美国说唱歌手学习
接下来一章是由主编金淑荣与韩国音乐评论人金泳大(Youngdae Kim,音译)写的“防弹少年团现象”。两位作者认为防弹少年团通过讲故事展现真实的自己是防弹成功的原因之一。两位作者强调,在防弹之前的韩流团体更多是完成公司指定的角色,而防弹歌曲里呈现的是更加真实的自己,并将这一状况与西方流行音乐里强调的“真实性”进行比较。不过,尽管如此,两位作者仍然强调防弹有其他所有标准韩流团体的基本特征,而他们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歌词将自己的处境表达出来,特别是在一些说唱歌曲里大胆使用韩国地方方言。两位作者因此认为,正是这一情况使得防弹能成为“本世纪的声音”。与此同时,二位作者还运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的《叙事经济学》(Narrative Economics)的理论概念对防弹歌词的成功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强调防弹歌词符合席勒研究的走红叙事的机制。因而,两位作者进一步反思了偶像和艺术家这一韩流产业里最本质的张力。

席勒2017年在位于黑帮说唱音乐drill发源地附近的芝加哥大学的演讲,强调经济学家最不重视叙事
与前两章关注防弹本身不同,接下来的一章是研究防弹的粉丝。由研究当代美国文化兼及韩流研究的北卡罗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康蒂丝·埃普斯-罗伯森(Candace Epps-Robertson)所写的“跨文化粉丝现象:防弹少年团与阿米”把韩流粉丝现象放到更大的粉丝现象背后进行考察,强调粉丝现象是流行音乐的一大本质特征,也强调在西方国家,大家一般对韩流粉丝的诸多偏见带有厌女症与排外症特征,即大家不理解由女性占主导的粉丝行为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埃普斯-罗伯森对从徐太志与孩子们出现的粉丝现象到现在全球化的粉丝文化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一方面,埃普斯-罗伯森强调韩流产业对粉丝组织的建立、经营与管理;另一方面,埃普斯-罗伯森也着重关注了粉丝组织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成员们会积极支持偶像的音乐产品与销售。同时,埃普斯-罗伯森特别强调了全球粉丝们积极无偿翻译和韩流有关的新闻与韩流歌词。此外,埃普斯-罗伯森还探讨了粉丝组织的公益与政治活动,尤其是防弹粉丝组织阿米对黑命贵的支持。
最后一部分“K-pop传播途径”包括三篇文章。首先是多伦多大学的媒体研究学者米歇尔·曹(Michelle Cho)写的“K-pop与参与的条件:替代性、连续性效应以及真实生活内容”。这篇文章从防弹少年团队长金南俊在一次采访里强调防弹音乐和视频从“真实生活内容”出发,曹介绍了媒体研究里的“替代性”(vicarity)、参与文化以及性别理论,强调韩流产品如何为全球粉丝提供了一个超越东西方的跨文化消费媒介。曹对粉丝消费的数种类型,特别是对记录粉丝观看偶像表演反应的视频、防弹少年团早期使用的“防弹Vlogs”以及娱乐公司发起的韩舞翻跳挑战赛进行了探讨。最后,曹强调K-pop为思考媒体理论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接下来的文章则是澳大利亚的麦考瑞大学专注日本性别人类学研究的托马斯·鲍迪奈(Thomas Baudinette)写的“偶像CP文化:探讨K-pop粉丝的酷儿性别机制”。基于对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鲍迪奈研究粉丝对K-pop男团偶像进行CP配对的现象是怎么成为表达性别认同的一种方式。首先,鲍迪奈介绍了韩国通过漫画形式给男团偶像进行CP配对这一文化是如何在日本同性漫画的影响下形成,强调这一行为是1990年代后韩国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建构女性空间和想象的一种方式。接下来,鲍迪奈介绍了日本韩流粉丝在少女漫画的机制下为K-pop偶像进行CP配对。鲍迪奈特别强调,在日漫和CP的机制下,K-pop已经是日本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如果说CP在日韩较多与日本发达的少女漫画文化相关的话,通过对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案例介绍,鲍迪奈强调,在这两个英语国家里,对K-pop偶像进行CP配对则成为直接表达性少数认同的一种方式。
在最后一章,由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吴柳郑(Youjeong Oh,音译)写的“循着防弹少年团的脚步:K-pop旅游产业的全球兴起”对防弹少年团影响下的韩国旅游业进行了系统介绍和分析。吴柳郑强调,韩国流行文化对外输出的一个结果是大量全球游客涌入韩国,对和流行文化相关的地点进行朝圣式旅游,防弹少年团是与韩流相关的主题游之一。吴柳郑进而介绍了大黑公司旧址、防弹成员练习生时期吃饭的姨母食堂(Yoojung Sikdang)、防弹早期专辑《最美花样年华》里面的拍摄地点、防弹成员去的咖啡馆以及防弹成员家乡的旅游。吴柳郑强调,粉丝对大黑公司旧址、姨母食堂的朝圣之旅尽管不符合一般意义上的网红打卡行为(因为这些地点都不够潮),但这恰恰是防弹早期通过向全球粉丝讲述自己作为小公司成员的困境的成功之处,粉丝们通过对这些地点朝圣去想象与防弹的亲密关系。

姨母食堂
总体上,这本包括17章的书涵盖了到2022年为止K-pop现象的基本方面,无疑会成为接下来数年内在英语语境下进行K-pop研究的首要参考书目。里面文章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引申为进一步研究,写成期刊论文甚至是博士论文。比如,在第二章里申贤俊提到的韩流产业里的胜者为王现象,鼓励K-pop历史研究者进一步跳出三大娱乐公司的叙事框架,去深挖更客观的K-pop的早期历史。同时,这一强调也提醒了研究者,关于目前全球K-pop粉丝群体里的K-pop历史是如何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无疑可以与德国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名著《文化记忆》进行有效互动,强调K-pop粉丝与产业形成的集体文化记忆。而李郑闵创造性地将声音研究带入K-pop研究,强调了在当下K-pop作为一种视觉文化情况下被忽略的听觉层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声音研究是否也有助于帮助研究作为K-pop视觉文化一部分的韩舞,即韩舞翻跳是否也可以理解为K-pop粉丝用身体的形式去回应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K-pop声音(比如在国内舞蹈工作室韩舞课上,老师都会问有没有“听懂”音乐)?同样的,就韩舞研究而言,吴周妍与瑞利智都注意到韩舞翻跳是一种社交媒体舞蹈,但她们关注点都在舞蹈而不在媒体。相反,在米歇尔·曹的媒体研究关怀下,认为与粉丝反应视频一样,韩舞翻跳是一种观众和媒体的有机互动。这又表明,舞蹈研究与媒体研究的结合存在更大的可能性,将韩舞翻跳放在粉丝对K-pop媒体产品消费更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即国内粉丝说的“扒舞”)。因此,这本书的各章节虽然由不同作者所写,但这些章节之间都或多或少存在潜在对话性,而这些潜在对话性,又暗藏新的研究题目的可能。
当然,作为剑桥指南的一部分,受到出版篇幅限制等先天因素,这本指南不可能面面俱到,很多章节也无法对很多问题进一步展开。对此,读者可以参考其它相关论著。对于早期韩流历史,第一章的作者马里昂凯在此之外写过数篇文章,崔慧恩(Hye Eun Choi)2018年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博士论文《殖民时期韩国音乐录制产业的形成,1910-45》(The Making of the Recording Industry in Colonial Korea, 1910–1945)则是对殖民时期韩国现代音乐产业形成、发展的深入历史学探讨。对于韩舞,第五章作者吴周妍在去年刚刚出版了《韩舞:在社交媒体上粉自己》(K-pop Dance: Fandoming Yourself on Social Media)有更深入的探讨。对于韩国嘻哈传统,除了第九章作者金暻铉在2021年出版的《霸权模仿:21世纪韩国流行文化》(Hegemonic Mimicry: Korea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有更详细讨论外,还有克里斯朵·安德森(Crystal Anderson)的《首尔之魂:黑人流行音乐与韩流》(Soul in Seoul: African American Popular Music and K-pop)与宋明宣(Myoung-Sun Song,音译)的《韩国嘻哈:全球说唱在韩国》(Hanguk Hip Hop: Global Rap in South Korea)。对于防弹少年团歌词,第10章作者之一金泳大也有专著《防弹评论:综合乐评》(BTS The Review: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the Music)。对于韩流下的韩国旅游,最后一章作者吴柳郑则有相关著作《流行城市:韩国流行文化与地点宣传》(Pop City: Korean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elling of Place),为了解韩流影响下的韩国旅游业提供进一步参考。特别是,斯蒂芬·崔基于对韩流产业田野调查写的研究,可能会更为粉丝读者感兴趣,这方面进一步文献可以看崔2018年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博士论文《韩流里性别、劳动与亲密关系的商品化》(Gender, Labor,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Intimacy in K-pop)。同时,陈达勇(Dal Yong Jin,音译)与韩国记者李俊(Hark Joon Lee,音译)于2019年合作出版的《韩流偶像:流行文化与韩国音乐产业的兴起》(K-Pop Idols: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Korean Music Industry)里也有对韩流产业里练习生的第一手田野调查和对相关舞蹈音乐老师的深度采访。
另外,缺少对K-pop在世界各地状况的专题介绍,可以说是这本书最大一遗憾(只有像李苏琳介绍Z-Girls时,介绍了一些东南亚的情况;鲍迪奈在研究CP现象时,又介绍了一些日本、澳大利亚与菲律宾的情况)。相反,对于防弹少年团过多的介绍(与此同时,缺少其他任何偶像团体的专题研究)又不可避免带入美国中心色彩(吴周妍文章里对各种男团女团舞蹈视频的介绍可以说是关注偶像团体最多元的一篇)。而对于这种以防弹为中心的K-pop研究,指南里一些作者都有间接反思,比如李苏琳在相关章节里就发问过,美国是不是K-pop的最终归宿?同样的,金淑荣和金泳大在合作章节结尾也期待K-pop的后防弹时代的到来。对此,需要更多的对K-pop在世界不同区域的专题研究。而就韩流在中国问题,读者可以参看孙美辰2022年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博士论文《从H.O.T.到GOT7: 中国的韩流粉丝、媒介与表演》(From H.O.T. to GOT7 : Mapping K-pop's Fandom, Media, and Performances in China)。
当然,防弹少年团代表目前韩流产业在世界形成的最大的影响,关注防弹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就防弹所属的HYBE公司对SM公司股票的购买无疑是韩娱圈今年年初的重要新闻,在此背后,HYBE从一个只有防弹的小公司发展到今天韩国甚至是全球娱乐行业里的巨无霸,这无疑值得结合韩国乃至全球资本主义变迁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可以在此基础上,从作为名人研究的防弹研究进入防弹现象背后的经济学研究。当然,对韩流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不一定需要像金久用那样对韩流产业进行形而上的批判,而可以在新自由资本主义批判的视野下,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这一对韩流产业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也可以对其它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一种经济学关怀下的视野。就拿HYBE公司下属男团TXT于1月发布的新歌《Sugar Rush Ride》来说,这首歌的音乐视频讲述了TXT成员遭遇船难来到一个岛上,在岛上,大家被其花朵及其它植物所吸引而流连往返,在克服了诱惑后,才下定决心搭乘重新搭好的小舟离开。熟悉欧洲文学传统的读者可以立马察觉到,这首歌借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的岛屿与食花者母题,而这个母题不仅是铁器时代希腊殖民扩张的诗学表现,也被近代欧洲殖民扩张所借用。可以说,就在HYBE公司有可能吞并SM的过程中,发出了这样一首歌,无疑表现了HYBE资本扩张的野心。古典学里有“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关注古典文本与母题在现当代文学文化的接受及运用(包括当代流行音乐)。自从防弹少年团2019年的歌曲《狄奥尼索斯》(Dionysus)因为对古希腊酒神文化的运用而引起美国的古典学家关注K-pop现象后,像《Sugar Rush Ride》这样对古希腊罗马母题有接受的K-pop歌曲越来越多,这些都为古典学与韩流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Sugar Rush Ride》里表现的荷马式的海难与花的诱惑
与此同时,K-pop的经济学视角也有利于思考更深的问题。李郑闵在对K-pop音乐风格的章节里,对K-pop音乐风格是基于韩流产业的需要就表现出一种敏感度,即音乐风格的变迁只是表象,而背后是韩流产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K-pop的音乐舞蹈风格(或者李苏琳强调的“K-pop视觉性”)成为了韩国影响下的全球晚期资本主义的美学形式。通过对当代美国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现象进行深入反思,著名文化批评家、芝加哥大学教授Sianne Ngai反思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美学表现形式。K-pop研究者完全可以像Sianne Ngai那样,把K-pop研究和批判理论进行进一步结合,去进行理论建构。特别是,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的一书在1989年出版时,还基本处于前网络时代。K-pop则有很大可能去帮助思考社交媒体时代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美学形式是什么。正如金淑荣在前言里强调,K-pop的发展与流行音乐的社交媒体化的发展是同步的。从一个黑格尔-马克思式的理解而言,我们可以说,K-pop已经不是一种社交媒体文化(a kind of social media culture),K-pop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交媒体文化本身(the social media culture)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当然,在K-pop研究里,新自由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批评只是一个视角,不一定成为一种目的本身。可以说,这本书的各章的作者们都没有谁是柏拉图对流行音乐批判的继承人。虽然如开始所说,柏拉图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早的流行音乐评论者,但在柏拉图生活的公元前4世纪古典希腊,柏拉图对流行音乐的批评并不是唯一的声音。大约与柏拉图同时期的古希腊作家色诺芬(按照传统,他像柏拉图一样也受教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算是师兄弟)写有《会饮》(Symposium)。在柏拉图的《会饮》里,苏格拉底直接让宴会里的吹笛女离开,而在色诺芬的笔下,苏格拉底在宴会上高度赞扬在宴会上表演的流行舞者,甚至还要模仿他(她)们跳舞。尽管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无疑是柏拉图对流行音乐的批判占据上风,但色诺芬笔下喜爱流行舞蹈的苏格拉底并没有销声匿迹。在公元2世纪,当来自叙利亚的罗马作家卢西安在《论舞蹈》(De Saltatione)里尝试为罗马流行舞蹈正名时,对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进行了“招魂”。卢西安这部《论舞蹈》在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味的场景,对话者之一卢西努斯(Lycinus)告诉另一对话者卡拉托(Crato)他刚刚从剧院看了流行舞蹈表演回来,卡拉托指责卢西努斯这样有教养的人不应该去看舞蹈表演,但在卢西努斯的说服下,卡拉托最终意识到流行舞蹈的价值。

跳舞的苏格拉底
因此,柏拉图无疑不会喜欢K-pop,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问:卢西安会不会喜欢K-pop?根据《论舞蹈》,答案很有可能是会的。在18世纪芭蕾舞还不被欧洲主流看好时,卢西安的《论舞蹈》就被拿出来为芭蕾舞正名,造就了19世纪以来芭蕾舞处于舞蹈金字塔尖的地位。在当下K-pop全球升温时代(还有与之伴随的韩舞翻跳的流行),重新温习卢西安的《论舞蹈》无疑会为这部古代文艺理论著作提供新的活力。特别是,卢西安强调,公元前5世纪的苏格拉底没有那么幸运看到舞蹈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所达到的发展高度。按照卢西安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公元2世纪卢西安没有那么幸运看到在公元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里的社交媒体时代下韩舞翻跳推动的全球舞蹈热。

卢西安
最后,卢西安写作《论舞蹈》的一个背景是思考第二次智者运动里的希腊知识分子能从罗马流行舞者的成功那学到什么。按照同样的逻辑,即使对不关心流行文化但关心和思考中国人文学术未来的中国学者而言,《剑桥K-pop指南》展现的韩国音乐人们怎么从单纯模仿、介绍欧美音乐到向欧美输出自己生产的音乐的图景,对于思考中国人文学术的未来也许并非不无裨益。在2021年,《指南》作者之一金暻铉的著作《霸权模仿》出版后,我和研究古典学在中国的芝加哥大学的古典学家莎迪·巴奇(Shadi Bartsch)发邮件说,中国学者从事包括古典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其实也不可避免是一个“霸权模仿”的过程,巴奇表示非常同意。回到《指南》主编金淑荣的前言标题“舞台灯光下的韩国时刻”,中国人文学术对西方学术数十年的翻译、模仿、吸收以及逐渐开始学会创造性发挥,最终未来是否会开花结果为“人文学术的中国时刻”,在理论上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