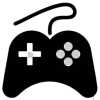文/宋彦
像是某种补偿,我总能在飞机上睡个好觉。
最近一次是在从上海飞去莫斯科的路上。那天,飞机上空得很,我一人占了整排座位。这是一次匆匆忙忙的旅行,机票是前一天才订的,下了飞机要去哪儿也毫无头绪,唯一确定的是,接下来的六七个小时能安安稳稳。
机载系统里有电影院正在重映的《阿飞正传》,随便点开,插上耳机,看张国荣泡一脸傲娇的张曼玉。手边的咖啡一直在喝着,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也不知道。只记得电影一直循环,每次迷迷糊糊醒来都是不同的片段,有一次是张国荣去找养母吵架,一次是刘嘉玲哭丧着脸拖地板,再一次好像是东南亚的热带雨林,配乐也让人迷幻。一整排空着的座位陆续有人来坐,有时是女人,有时是俄罗斯胖大叔,唯一让我眯着眼多看了两眼的是个裹在红色耳机里的金发小帅哥。
机舱里昏暗的光线,国语、粤语轮番放着的老电影,还有每次醒来见到的不同人,时间像是被无限拉长了。至今回忆起来,我都不知道这些场景是冗长的梦,还是被浪漫化的现实,总之,这段飞行占据了我俄罗斯之旅的三分之一记忆。
这并不是我在飞机上的常态。更多时候,只要坐在那儿,我就能瞬间睡去,睡得昏天黑地,连飞机起飞都不知道。
都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能在各种交通工具上踏实睡觉,这大概是上帝在剥夺了一夜夜好眠后,留给我的那扇窗。
大学四年级时,我第一次丢失了睡眠。不明原因,没有征兆。后来和很多失眠的同龄人聊起,大家都觉得,睡眠这东西就像是恋爱中总在付出的那一方。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主动追求你,向你献殷勤,变着法地对你好,但你哪里懂得珍惜啊,你浪荡漂泊,花花世界还没看够,哪舍得睡去。总有那么一天,它倦了、烦了、绝望了,转身离你而去,留你在原地追悔莫及。大多年纪轻轻就失眠的人都经历了这个与黑夜相爱相杀的过程。
那段日子,我经常躺在寝室床上,看从窗帘的缝隙里透出的那道光。窗外的小花园里有很多野猫,到了晚上就开始浪叫,像小孩的哭声。寝室里有个姑娘会说梦话,不是喊两声那种,经常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听到了我就用手机记下来,第二天再念给她听。大多数校园爱情的吵架和分手都在深夜,每次后半夜在走廊里溜达,都能碰上一两个躲在墙角打电话的人,有的哭泣,有的决绝。
当时还没有微信,大家靠QQ建立和维系各种情感。实在无聊,我就用手里那台紫色诺基亚E72i登录QQ,看看谁在线,能一起消磨这漫漫长夜。总有个头像是亮着的,我们胡扯着等来了很多次天边泛起的蓝光。这当然不是个爱情故事,这是坚不可摧的革命友谊。
发现可以在交通工具上睡觉是大半年之后的事了。那阵子,经常要往返于家和北京,对穷学生来说,火车卧铺是最不浪费时间又经济实惠的选择。躺在各种主食、茶水、包裹味交杂的车厢里,总有一阵“我为什么在这儿”的厌恶感。随着火车开动,这情绪意外地渐渐褪去,车轮与铁轨发出有节奏的撞击声,若躺在床上,这分贝是刺耳的噪音,但在移动的火车上,这声音让人踏实。窗帘拦不住所有的光,忽明忽暗的车厢,再配上“将去远方”的幻想和模糊的意识,人容易产生穿越时空的错觉。这时,我总能好好地睡上一觉。偶尔也有意外,比如,遇上个呼噜震天的邻居,那鼾声会把人从时光旅行中瞬间拉回现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失眠带来的焦虑感会越来越强。二十出头,你觉得那是种很酷的小毛病。在网上随便搜索,你知道天赋异禀的艺术家、作家、导演们都失眠,好像获得了这个小毛病就预示着你将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焦虑是焦虑的,但窃喜大于焦虑。
但很多年过去了,你没能成为艺术家或者作家,只有失眠陪着你,这件事不仅焦虑,还丧气。
去年,我经历了一段这些年来最难熬的失眠期。从前的失眠是彻彻底底的睡不着,醒着看天亮,等人间重新罩上烟火气,那是个从低谷慢慢爬升的过程,失望里总有点希望。
去年那场失眠更像是睡眠对我的一次又一次欺骗。
难是难了点,但每天的两三点钟我总能照常睡去。为了制造黑暗,我有个厚厚的窗帘,拉上它就分不清白天黑夜。一觉醒来,觉得天亮了,伸手摸手机,按下解锁键——3点半。疑惑,再努力睡,睁开眼——4点。再睡,睁眼——4点40……
重复着这种“天亮了”的欺骗游戏,每次点开手机,都是失落中夹杂着愤怒。我们总是更能接受坦白的伤害,却对被揭穿的谎言不能释怀,这就是我和那段失眠期的关系。从那之后,我再不拉窗帘睡觉,亲眼所见的黑暗和天光比手机上冰冷的数字让人好受。
那阵子,我尝试了很多让自己多睡一会儿的方法。我喜欢上北京的堵车,出租车堵在东三环上,我坐在司机身后,不知不觉就会睡过去。一睁眼,40分钟过去了,车不过从三元桥移动到团结湖,还能再睡上40分钟。公交车也很好,随便上一辆,漫无目的。只要不是早晚高峰,北京的公交车总有座位,窝进去,看好背包,就能踏踏实实地睡到终点站。
电影院也是睡觉的好地方。说来惭愧,自从开始写电影报道,我在电影院里睡过去的概率越来越高,打得越激烈的片子,睡得就越深沉。住处附近有家百老汇电影中心,独立的影院,白天大多没什么人。如果前一晚睡得实在差,我就在第二天下午随便买一张电影票,大多是两三点钟的,后排,远离多数人。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有了着落,睡不睡都不强求,醒着就看电影,睡了就是意外收获。抱着这样的心态,总能睡上一阵子。睡醒散场,去隔壁咖啡馆喝一杯牛奶或者柠檬香橘茶,这难熬的一天就算过去大半了。接下来,就是难熬的另一半。那段日子,我的时间感很差,白天黑夜混在一起,脑袋里也混沌一片,整个人都像北京的雾霾天,阳光和氧气透不进来。
过了大概三个月,在安眠药和sleep aid的辅助下,这状况渐渐好转。我想了很久,为什么看似安稳的床没法让人好好睡觉,流动的交通工具和电影院却总有疗效。
大概因为,无论是交通工具还是电影院,它们的开始和结束都有期限。这有点像讨论绝对的自由和有限的自由。我的工作和休息时间自由支配,除了一个长线的deadline,没有被切割的任务,也没有被明确约束的时间。睡觉并不珍贵,它随时可以进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醒来后也没有明确的指令,这会让人陷入迷茫。
坐在飞机、火车、汽车上,在电影院里,在明确的地点和时间开始,清楚地知道它何时结束,可预测的时间,明确的任务,每根神经都可以懈怠一阵子,再被重新唤醒。
这大概是睡眠的奴性,也是我的奴性。或者,换个积极点的说法,这是睡眠的纪律,也是生活的纪律。从前我反抗它,现在,得选个漂亮的姿势缴械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