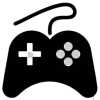一九七一年年底,学校新来了一位年轻的体育老师,孙世修老师。孙老师高中毕业后,回乡任代课教师,经过几年的历练,做了廒上联中负责人。他在体育方面有专长,一直缺少一个合适的平台,来施展他的抱负。
由代课教师转正后,分配到了海阳十一中,这一年他刚好三十岁。他来后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球场上多了一副篮球架。坑坑洼洼的球场,变平整了。乒乓球的设施也全了,有网又有球了。
原先,全校只有几只篮球,放在体育老师办公室,同学们玩的时候要到办公室要,特别不方便。现在,每个班都有一只蓝球,虽然质量差些,是带毛刺的塑料胶皮蓝球。
最大的变化,是建了新的运动场。早先的运动场,受地形所限很小,一圈跑道只有一百五十米,不伦不类。这种运动场在高中学校中是很少见的。
运动场的北面,是一片几米高的岩石,这片岩石自建校始就在那了,限制了运动场的发展,也无法构建其他设施。
孙老师说服了校领导,组织师生自行施工,两个多月后,生生的把这片岩石给搬走了。
那段时间,孙老师统筹安排,场地所限一次上一个班级,每班两小时,几个班级轮番上阵。土法施工,男生抡大锤打炮眼,个别学生和老师点火放炮,女生搬运碎石。想象不到,经过师生们的辛苦劳动,很快,两个多月后,平整出了一个新的运动场,而且是每圈跑道二百米的运动场。虽然不是十分完美,这在当年己是奇迹了。
学校每年举办两次田径运动会,新运动场落成后,正赶上要开秋季田径运动会。顺理成章,秋季田径运动会,在新体育场举办了。那是运动会的第二天下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故。
这一天从上午开始,径赛项目就进行的特别不顺畅,问题出在了小小的发令枪上了。可能是发令枪的纸炮受潮了,运动员在跑道上,做好准备起跑,只等发令枪响,哪知一声枪没打响,虚晃了运动员一下。
又重新回到跑道上,做好准备,只听发令的孙吉坤老师喊:“各就位”,“预备”,又一枪哑炮。有时几次都无法正常发令。枪经常打不响,有时打响了,声音也不清脆,滋滋冒火花。这就严重影响了运动员的比赛节奏,也影响了运动成绩。运动会开的很拖沓。
下午,场边观赛的同学们也有了疲劳感,注意力不在运动项目上了,在各自玩自己的。正在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发令区旁边的同学们一阵躁动,我离的不远,挤过去一看,化学老师李延旭躺在地上举着一只血淋淋的手,孙吉坤老师半蹲着,双手使劲掐住李老师的胳膊,李老师的手己不见了,只见鲜血汩汩往外冒,只听孙老师大喊:“快点,快点,我掐不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惨烈的场面,只见了一眼,心里就接着一紧,马上一扭头,再也不敢看了。后来怎么叫的救护车,怎么抬担架上车,怎么送的医院,到医院后又怎么转院到了海阳县医院,现在己完全没有印象了。
十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班的同学们自发的组织去医院探视李延旭老师,看到李老师的手残疾了,但精神状态还不错,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还原一下事件的基本过程。当时发令枪打不响,影响了运动会的顺利进行。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很着急,想了很多方法都不奏效。
这时候化学老师李延旭,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回化学实验室合成了炸药,他试了一下,效果很好。取出一点点,用锤子一敲,呯的一声,响声很干脆。
运动场上,众人正在为发令枪的事烦脑,只见李延旭老师手拿一只玻璃量杯,说:“来了,来了”,孙世修老师高兴地说:“哎呦老李呀,你有这好东西,怎么现在才拿出来”?话音未落,就响了。
当时发令枪刚打过一哑枪后,放在桌子上,李老师手拿量杯正好走到了桌子旁边,枪在滋滋往外冒火,李延旭老师一见不好,就用另一只手去挡,但己经来不及了,惨案就发生了。
李延旭老师,是个教学水平很高的老师,授课中经常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小怪招,使枯燥的化学课生动有趣,同学们称他“怪”。
可惜了,自这次事件后,就消失在教学岗位上。李老师有个小儿子,当年六、七岁,长得和他一模一样,同学们称:“老李和小李”。老李和小李经常一前一后在校园里走着,场面很滑稽,现在脑海中还能浮显出这美好的画面。
记得自孙世修老师来后,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田径运动成绩在海阳一中之后居第二位,各项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在体育方面,凭一人之力,改变了一所学校。孙世修老师后来做了海阳体委主任,这也可能有在海阳十一中工作成绩的助力吧。
在高中期间,有一门课程,是我最怕上也最不想上的。每次上课前都压力很大,心中忐忑不安。这门课就是音乐课。
教音乐课的,是姜丛祥老师。姜老师说话慢声细语,对待学生从不严厉,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我不想上音乐课,并不是说姜老师教的不好。从现在的教学方法看,当年姜丛祥老师的教学水平很现代,现在很多先进的英语教学都和姜老师的方法类似。
每节音乐课都有“视唱练耳〞环节,开玩笑啦,哈哈哈,没有那么高级,没有“练耳”只有“视唱”。
当时的音乐课很简单,就是音乐基础知识,识简谱。每节课最后都有视唱环节,老师课堂提问,学生站起来唱。
我自小害羞,从不敢在人前唱歌,没人的时候还瞎哼几句。每节课老师到了这个环节,都要点名学生起来唱,这次叫这几个人,下次叫那几个人,轮换着来。这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时候,生怕老师点我的名,我用力低着头,经常看到老师的目光巡视一圈,看到我这里停留一会,我的头会越埋越低,有时都好低到裤裆了。
可能是,姜丛祥老师也发现我的冏态,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我一马。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毕业,姜丛祥老师也一直没叫我起来唱。每节音乐课都是我的一道坎,上一次遭一次罪。
我觉得这一学期,老师没有点名的同学没有几个,我算是其中之一吧。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这一幕,也觉得自己很可笑。